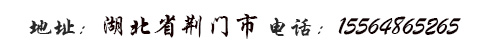随风而逝一段乡村生活,一条朝圣之路
| “夏的头一天,我随着风来;秋的最末一日,风将带着我去。”——阿巴斯《随风而逝》是一部非“主流”的电影:拒绝动作,排除剧情,没头没尾。剧未终了,观众或已熟睡。影片的内容很“反叙事”:几个工程师似乎抱着某个目的来到伊朗一个小村子借住,影片围绕其中一个工程师巴扎在村子里的所见所闻展开,非常平淡、生活化。没有前因后果,只有生活片段。而这正是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个人特色。阿巴斯是伊朗新浪潮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电影手册》评价他:“创造的影像标志着当代电影每年都在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在电影大师马丁·斯科塞斯眼里,阿巴斯“是那种对这个世界拥有独特认知的少数艺术家”,让·吕克·戈达尔对其评价更为振聋发聩:“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在电影界,阿巴斯无疑是一位有着伟大成就的独立电影人,这不仅仅是源于阿巴斯对电影新形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倾注的哲思。1、关于生与死的探讨,以及展现出的生死观:生死交替,循环往复纵观来看,阿巴斯在他的电影中喜欢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拷问,这一特色在越靠后的作品中越为突出。这是有原因的。年6月,伊朗北部发生大地震,数万人遇难,阿巴斯获悉后,带上自己的儿子驱车前往地震中心地带,想要寻找自己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主角。一路上,他的目光没有聚焦在死亡上,而是被那些顽强的幸存者所吸引。这给了他的心灵很大的震撼。在自己的书中,他谈到:“在地震现场,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去那里不是为了观看死亡,而是为了发现生命。”根据这段“地震之旅”,他拍出了动人心魄的《生生长流》,基本是自己这段经历的重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这场发生在他生命中的地震带来的“余震”:拍摄于年的《樱桃的滋味》通过一位自杀的人来探索死亡的主题,而这部拍摄于年代《随风而逝》,也通过影片中一位濒死的老太太和由于塌方被活埋的人,探索了生与死的问题。《随风而逝》中有一位自始至终并未出境的老太太,她身患疾病,濒临死亡,巴扎到村子的第一天,安顿好住宿,第一时间就跟小向导发仔询问老太太的情况;第二天他去咖啡馆喝咖啡,濒死老太太的儿子也在,后被家人叫走,巴扎见状跟着他走,匆忙中相机都忘在了咖啡馆;随后几天,他每次见到小向导之后都要询问老太太的情况,在与老板古达兹夫人通电话时谈论的也都是濒死老太太的情况,似乎在等待着她的死亡。虽然导演并未说明巴扎一伙人到这个村子的原因,但我们有理由推测来村子的目的跟濒死老太太有关。在村子里,他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是爸爸打来的,我们依据巴扎在电话中的回应,可以推测爸爸打电话是来告知某位亲戚去世了,但巴扎此时的回应是:“真的很遗憾,那么哀悼吧。如果有人问起我,你就说联系不到我,反正他们不知道我买了手机,服丧的第七天我就会回去了。”他有些不耐烦的挂掉了电话,此时他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是轻蔑的。而到了后来,他的态度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当同伴们等待多天后仍不见濒死老太太死亡,敦促巴扎做出决定时,巴扎此时已经向濒死老太太那边倾斜,不愿意主动做出计划(很大可能是谋杀);当看到挖坑人被埋时,他开着车四处叫人来解救;在碰到医生后,他主动说起濒死老太太的疾病,邀请他去救治。巴扎对生命和死亡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许是感动于挖坑人的淳朴、善良;或许是惊讶于挣扎翻壳的乌龟以及搬运粪团的屎壳郎的生命力;抑或是因为看到刚生完孩子就工作的妇女、背的草完全覆盖住身子的妇女那种对生活的忍耐力……而投放在微小事件上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使微小不再微不足道,“反而被发掘出隐藏在其表象下的古老而深沉的哲学。这种哲学强调的是生生不息。”除此之外,影片还含蓄地表达了阿巴斯的生死观。影片中有很多关于死亡的意象,比如从挖坑人那里拿到的腿骨、濒死老太太、黑暗、古达兹夫人的电话等等,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生之意象:婴儿、羊群、小狗、麦浪等等,它们统一和谐于这个世界中,交替往复,生生不息。导演在调度生之意象与死之意象时,喜欢让它们接替出现。比如他三番五次驱车前往打电话的高处,其实是一块墓地,旁边种着枝繁叶茂的大树;每当他驱车前往高地接古达兹夫人的电话,下一个镜头往往就是儿童牧羊;而影片最后,巴扎将腿骨抛进河流,镜头随水流而下,岸边是啃草的小羊。阿巴斯曾说自己喜欢的一位诗人是古波斯诗人海亚姆,他这样评价海亚姆:“他的四行诗就是对生命的永恒礼赞,但却伴随着无处不在的死亡,死亡帮助他握住了生命。”生命伴随着死亡,生生死死交替出现,循环往复,这也正是阿巴斯在《随风而逝》中展现出的生死观。2、关于“传统信仰”和“现代”之间的讨论某一次巴扎接完电话,驱车回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对朝圣的意义产生怀疑的年轻人。他与巴扎讨论自己母亲脸上因为朝圣留下的伤痕:“第一道伤痕,是为我姑姑的死,我可怜的妈妈这样是为了表达对我爸爸的爱;第二道,是为了我爸爸工作的厂里的老板,他的一个亲戚死了,这样我爸爸才不会失业。我妈妈服了很多丧,她牺牲她的脸,我真不敢相信……我对这样的事不感兴趣,当我想起这样的事,我只感到痛苦。我想朝圣的起源一定要变得更经济点才是。”在这段路途中,巴扎对于朝圣不发一言,每当小伙子问他对此怎么看的时候,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濒死老太太死后,记录这一“愚昧落后的传统”。在到达村子后与古达兹夫人的第一通电话里,巴扎将说未说的话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当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真的对这一传统产生质疑,认为应该将朝圣变得“经济点”的时候,巴扎的心情又是复杂的。把年轻人送到学校后,他把小向导发仔叫了出来,发仔说自己还没有做完题所以不能跟巴扎走,而那道题是“在审判日那天,上帝和魔鬼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巴扎脱口而出:“很简单的题目,上帝下了地狱,而魔鬼去了天堂。”脱口而出后,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又改口道:“上帝上了天堂,魔鬼去了地狱。”受教育的年轻人和儿童代表着社会、国家的未来,而影片中这位年轻人对于朝圣的怀疑以及发仔对于“审判日”问题的求助,都显示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信仰缺失。这让人想起尼采的那句“上帝已死”,它标志着宗教的土崩瓦解和世俗化潮流的滚滚而来。而良善的村民无疑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巴扎去高地打电话遇见的挖沟的人,当巴扎形象化地说起自己的工作因为没有“镐”而遇到了困难,单纯的挖沟人说“我可以给你一把镐”;当他拿着羊奶罐准备去卡克·让哈曼家取羊奶的时候,却错去到了他的邻居家,但是邻居拿过羊奶罐就要给他挤羊奶,正如挖沟人所说的那样“村里任何一户人家都会给你羊奶”;从卡克·让哈曼家取完羊奶,主人将他支付的钱又还给他。正是这些良善的村民让巴扎对待生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而代表着“利益”、“现代”的老板和同事们,却在等待甚至期盼一个老太太的死亡。阿巴斯在影片中并没有对两者进行过多地褒贬,他将自己的态度展露为对古老民族文化的皈依。3、一个人的“朝圣”之路当巴扎从发仔口中得知老太太好一点了,原本等待她死亡的叔叔回到科曼莎请假,以回来照顾老太太的时候,巴扎的“利益之心”、“现代之心”松动了。发仔口中的叔叔,原本跟巴扎是一类的人,因为受过教育在城市工作,脱离乡村、传统已久,充斥脑中的大多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回到这个落后的乡村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等待濒死老太太的死亡。所以当听到发仔说他的叔叔“哭了”,并且回到科曼莎请假以继续回来照顾自己母亲的时候,原本是“同一战线”的“同志”脱离了,巴扎才有了自己是不是坏人的询问。这其是对自己一直信仰的“现代”、“利益”等潮流事物的怀疑。接下来的一个场景是巴扎怅然若失地坐在那里,一个腰几乎弯成九十度的老妇跟巴扎问好:“愿主给你骄傲,愿主给你健康,愿主保佑你长命。”驼背老妪是一个寓言性的所在——她出现在巴扎对自己一直以来所信仰的事物产生怀疑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的时候。影片还有一个暗喻性的细节:影片末尾,当巴扎又一次开车前往高处接电话时,在路上碰见了跟自己一起来的几个同事,他们对巴扎说:“不要去朝圣了,过来吃草莓吧。”巴扎当作玩笑话摆摆手。朝圣,一般来说是宗教信仰者为了表达自己对宗教的忠诚,有时也被称为“在人间满是眼泪的山谷里游荡”,朝拜圣地常常是使徒遗骸的安放地,而巴扎三番五次开车前往的高地也是一块墓地。这个一语双关其实暗示了巴扎一次次驱车前往墓地,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接打电话,更重要的,这是他的认知之路,朝圣之路。正是在驱车前往墓地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挖沟的善良淳朴的村民,看到了挣扎翻盖的乌龟,推动比自己体积大很多倍粪团的屎壳郎……在所见所闻所感中,他体认到生命的顽强与珍贵。阿巴斯在访谈中说道:“路表达了人们寻找必需品,寻找永远不安的灵魂,寻找永不结束的探索。”蜿蜒之路其实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着生命旅程。也正是在这条朝圣之路上,巴扎完成了自己对生命与死亡、传统与现代等问题的思考与选择。巴扎通过在蜿蜒之路上的一次次见闻、感悟触碰着社会和人性,完成了自己对生命与死亡、传统与现代等问题更为宽广成熟的认知。影片最后,当巴扎将腿骨抛入自然的河流后,人骨随水波流转,正如本影片的名字“随风而逝”,死亡伴随着新生,悲哀处也有快乐涌动,正所谓“现世浮华,游历苦行,热爱本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langtuhao.com/ylthxf/11155.html
- 上一篇文章: 食物的魔力通过吃,培养孩子探索世界的
- 下一篇文章: 随着制裁的解除,伊朗耸耸肩我们才是世界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