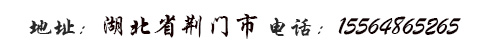YC铁穆尔让我去马马耶夫山冈吧
|
在马马耶夫山岗那边 “河谷里的笨蛋们,让我去马马耶夫山冈吧……”。 不知是源自一个梦,还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或是一部二战电影中有人在这样喊。“马马耶夫”这个名字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当然那一年我去俄罗斯并不是因为马马耶夫这个名字才去的。 马马耶夫这个俄罗斯化的名字,来源于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及其子拨都汗的后裔马麦汗。马麦是金帐汗国的贵族,从他的时代开始,金帐汗国日益式微。马马耶夫山冈在蒙古语中叫做“马麦汗·套勒海”意为马麦可汗的山冈。这个名字体现了不同族群的语词交汇融合。年秋,我们从莫斯科到了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曾一度叫做察里津和伏尔加格勒。汽车驶出斯大林格勒后,卡尔梅克蒙古学者热尼亚带我们到了伏尔加河畔的马马耶夫山岗。对于世界屋脊吐蕃高原的高山大河中成长的我来说,俄罗斯的马马耶夫山冈只是一个在东欧平原上常见的低矮山冈,是我的原乡族人叫做“皋图勒”的那种地形。这个小山冈据说是古代蒙古-突厥人的坟墓形成,我觉得形成时间也许更早。就因为成吉思汗后裔马麦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山冈有了大名。使他象征着最坚强最勇敢的战斗。而对于内亚游牧族群的后裔如我辈的眼中,南俄罗斯草原,斯大林格勒,马马耶夫山冈只是亚欧大草原的西端而已,是草原游牧人的旧地,是我们的祖辈自由自在放牧的家园。我知道南俄罗斯草原在古代的历史,清楚它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的关系,南俄罗斯草原在中世纪以后和阿瓦尔人以及成吉思汗的后裔密切的关系。如今,南俄罗斯草原对我来说更有一些只能意会的含义,而马马耶夫山冈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符号。 平缓的马马耶夫山岗上85米高的母亲雕像,是世界上非宗教和神话最高大的雕像。苍天在垂泪,母亲在挥剑呐喊。 热尼亚和作者在马马耶夫山冈 热尼亚和我并肩走在山冈上,他指着母亲雕像对我说eikinotohktodana.。他用伏尔加河畔的蒙古语方言说的这句话,可以译为“祖国母亲在呼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生死攸关的惨烈战役的纪念。马马耶夫山冈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主战场,因为控制了这里就可以控制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运输线。夏天到年冬天在这里的一系列战役中双方死难约两百万人。我们在马马耶夫山岗下的红军纪念碑广场徘徊,在风中瞭望斯大林格勒市和伏尔加河。 “eikinotohktodana.” 在俄军中服过兵役,在欧洲和亚洲几个国度闯荡江湖的卡尔梅克蒙古学者,见多识广老辣之极。听着卡尔梅克朋友们俄语和蒙古语的交谈声,我想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悲剧可汗马麦,还是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地球上,另一个类型的战争自有了人类以后从来就没有停止,那就是——语词的战争。 伏尔加河 我和ANUU站在石头上,把白色的哈达放在水面上,献给了伏尔加河。我们乘坐的汽车一直向南奔驰在秋风中,这里是伏尔加河以西,黑海以东,高加索以北的原野。进入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从车窗里看着卡尔梅克蒙古人的房子、畜圈、牛羊。平坦、辽阔一如蒙古高原。 在卡尔梅克人孟克和瓦丽亚夫妇家,在巴兹尔和维拉等朋友家中,除了奶茶和羊肉外,都是俄式西餐。伏特加、威士忌,还有各种红酒。在卡尔梅克的许多次宴会和交往中,亚欧大草原的话题,熟悉的语词和伏尔加河的风一起灌入耳膜,令人遐想。 伏尔加河口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列宁的祖母便是这里的卡尔梅克人。当年土尔扈特蒙古的和鄂尔勒克汗带骑兵围攻这个里海北岸的城市,围了几个月没有攻下来。因为当时城中的火器太猛烈。关于卡尔梅克蒙古人的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书籍不少,没有必要在此赘言。 阿尔巴特街头艺术家 瞧,阿特拉斯罕古城的公园里,表演俄罗斯古风的俄罗斯人围成一圈在唱歌。唱歌的姑娘们,鲜艳的服装,拉手风琴的男人,精制的马车。我还在阿斯特拉罕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一个木制的奶桶,这是鞑靼(塔塔尔)或巴什基尔牧人的用具,这个奶桶和我母亲打酥油的奶桶一模一样…… 最让我们久久回味的是埃利斯塔市郊外的一个巨大的黑色雕塑,那是纪念卡尔梅克蒙古人在那个麻脸小胡子的命令下流放西伯利亚的历史。黑色熔岩般的巨型雕塑,悲鸣的马、火车、森林、寒冷、饥饿和死难……一个多难而伟大的人民,这个“人民”已经不仅仅是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蒙古人,而是20世纪地球上所有苦难的人民。这个雕塑上刻着20世纪惨烈苦难的全部特征。伟大、阴郁、受难,为了在痛苦的大地上实现乌托邦而受难…… 卢比扬卡大楼 在莫斯科。天哪,我无法淡然注视,那就是血腥的卢比扬卡大楼,一栋八层巨型建筑。20世纪的上半叶,有多少人呵!被押解到卢比扬卡大楼的地下室后,被来自后脑勺的一枪,结束生命,一般用纳甘式左轮手枪。铺着沥青布的地面上的血迹很快会被清洗干净。又有多少人从那里出来后身心俱碎,沦为牲畜般的奴隶。1940年1月15日,伊萨克·巴别尔就是在这里被枪决的。20世纪以来的屠杀、暴政……其实,人类性格中最好的或最坏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远古,追溯到我们都没有任何族称任何语种的时候,追溯到人类的始祖。大多数人是不会关心真相的,麻木和冷漠是人类的通病。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也是我们的历史,人类就像树一样,表面看来是独立的,但树根是通过大地连在一起的。 卡尔梅克女学者达尔玛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多次去印度朝圣,聆听神圣喇嘛的讲经。她给我们讲述了年12月的卡尔梅克,苏德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年轻人大多都在各个战场上的红军部队中战斗,他们的父母们却被定为“有罪的民族”“法西斯的走狗”,流放在西伯利亚。被流放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牛羊在哀叫,/孤儿寡母和年迈的爷爷在哭泣,/火车在伏尔加河边飞驰,/人们被押送往西伯利亚……(斯·马祖尔克维奇《年12月28日》) 卡尔梅克人被押上列车后,他们的狗在后面追赶着列车,一直追着,直到累死在铁轨上。卡尔梅克老人、妇女和儿童们挤在寒冷肮脏的货运车厢里。每天,都有母亲们在已经死亡的婴儿旁边哭泣,到处是冻僵的尸体。他们成群地死于寒冷饥饿或疾病。他们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最寒冷的地区整整十三年,他们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阿尔泰边疆区,鄂木斯克,雅库特,萨哈林……等地,没有食物,炊具和房屋,有的人被押着关进牲畜棚,他们用偷偷藏在身上的首饰等值钱的东西换点食物和炊具。但是仍然饿死冻死病死许多人,父母死了,姐妹兄弟死了。因为没有冰冻的地面根本没有办法挖开,他们就把亲人的尸体匆匆埋进积雪里,春天雪化时尸体露出在地面上,春汛泛滥时,河水把尸体冲了上来。还有那些女孩的尸体,长长的头发还是像活着的时候那么漆黑柔软。活着的人牵着牲畜驮着那些尸体去埋进土里。那个泰加森林至今仍然叫“卡尔梅克森林”,因为有太多的卡尔梅克蒙古人死在那个泰加森林里。 年1月到2月,在前线和德国人浴血奋战的卡尔梅克红军战士和军官,纷纷被召回,被押送到了乌拉尔的建筑工地,当战士们得知自己的家属也被当做“法西斯的走狗”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时,绝望和悲伤“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也垂下了头”。有些战士从建筑工地幸运的逃脱后又返回了正在激战的前线,去战斗去牺牲,好一个草原民族的血性。更多的红军战士在各地的建筑工地或古拉格被折磨死去,在科雷马半岛,在西伯利亚,在北冰洋沿岸无数的古拉格集中营像牲畜一样死去。卡尔梅克诗人卡良桑吉就曾在科雷马集中营服刑,那里也就是著名的集中营作家瓦尔兰·沙拉莫夫服刑的地方。 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了年,苏共二十大后,被流放的卡尔梅克等族群被平反,幸存的人们陆续返回了支离破碎的家园。自治共和国也陆续恢复。但那些被折磨死去的人们呢?那一个个被摧残被蹂躏的灵魂呢?那一个个被丢弃在无名荒原上的骸骨呢? 就是从那个时代起,卡尔梅克蒙古人都开始大规模使用俄语名字和俄语俄文。达尔玛说,如果说卡尔梅克蒙古文化是珍宝的话,那么西部蒙古地区通用的托忒蒙古文就是金钥匙,而如今这把金钥匙被扔进了茫茫的黑海里。周围多是使用俄语的人,卡尔梅克蒙古语词汇渐渐显得贫乏。她说现在急需编纂一部高水平《卡尔梅克蒙古-喀尔喀蒙古-俄罗斯语的大词典》,他们正在编纂卡尔梅克文献的辞典,就是要让民众去使用文献中那些丰富的语词。唉!人类有多少文明就这样失落了,像那个被扔进黑海里的金钥匙。 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大多数学者用俄语发言,其次是英语,用卡尔梅克蒙古语发言很少,卡尔梅克蒙古语只限于会议祝辞等仪式。在卡尔梅克小学里,年迈的卡尔梅克老奶奶在认真教孩子们本族语言和习俗,举止大方气度非凡的孩子们在学习和表演中,极为投入而认真。在英雄史诗《江格尔》专家的后裔家,穿着蓝色卡尔梅克蒙古袍的老奶奶用温厚的手拉我过去看她的舅舅奥其尔先生——已故的史诗《江格尔》专家,曾在麻脸小胡子时期多次被捕入狱,最后是在她和她妈妈的照顾下去逝。在她家佛龛前拿出珍藏的苏鲁锭旗帜放在我们几个人的头顶上举行了仪式。念诵着卡尔梅克蒙古语的祈祷语词祝福了我们。她和家人用羊肉款待了我们。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书伏尔加河畔使用蒙古语的族群——卡尔梅克蒙古人对自己语言文化的感情,以及他们在欧洲强大族群中的挣扎。无论是在年的大规模流放和逮捕中,还是在东欧土地的日常生活中,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创造奇迹,这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语词的战争和语词的融合。语词间的战争和融合就是不同的文明或冲突或融合。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工作和学习的卡尔梅克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喀尔喀蒙古人、哈萨克人、塔塔尔人、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还有高加索诸族和其他众多族群。我能感觉到他们都有自己强大的灵魂和紧强的自信。 在俄语的海洋中。几十万人使用的卡尔梅克蒙古语在战斗在融合在高歌在欢笑,卡尔梅克人珍视自己的古代风物。这是人类精神和智慧的伟大和坚强。 呵!久违了的关键词 在埃利斯塔市,ANUU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从中国新疆迁居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蒙古人,乌兰巴雅尔和乌图娜生夫妇,那木吉勒和孟根夫妇等人。我们去埃利斯塔郊外的原野上,到英年早逝的新疆伊犁籍蒙古学者绰罗斯·额尔敦巴雅尔的坟墓,木制的墓碑已经被南俄罗斯草原夏天的烈日晒成了咖啡色,我们在他的墓碑上拴了一条蓝色的哈达,祭洒了伏特加,愿他的灵魂在这长满羽毛草的广阔原野上安息。 在宴席上,卡尔梅克人悠长的颂词开始了,接着开始喝伏特加和各种红酒果酒。卡尔梅克人比我们尧熬尔人更多地记住了自己的诗歌。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国立大学,ANUU用蒙古语介绍了远在吐蕃高原边缘群山的尧熬尔人,西喇尧熬尔人等。对许多卡尔梅克人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游牧的尧熬尔人。 “这位是尧熬尔……”。 接着是惊讶、善意和好奇的目光,好像是似曾相识在千年以前。那是古代的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那是神圣的鄂尔浑河于都斤神山…… 还是不必追溯太远。就是自匈奴时代,自从冒顿单于的五色骑兵集团军以后,自铁猴年()的大雪后,我们曾轮回了多少次。我们积淀了多少歌哭,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多少次死里逃生…… 我们的那些基于血液的浪漫华丽的语言,那些驾驭着人们全部心灵和感情的语词,如今这一切不仅变成了俚俗方言,而且语词渐渐贫瘠不堪。我说这不是因为轮回的次数少而变得贫瘠和浅薄。 有谁还记得那些关键词呢?如“尧熬尔”,如“博格达汗”“金格斯汗”如“兀鲁斯”“汗腾格里”“于都斤·额客”“额客·瑙套格”…… 呵!久违了的关键词!我曾在祁连山下的原野上,在那座烟熏雨淋的黑帐篷里喊哑了嗓子的关键词,远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人是熟悉的,中央亚细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熟悉的。祖辈留给我们的语词,告诉了我生活在亚欧大草原上的人们内在联系的奥秘。 另一部分语词却在膨胀和扩展,成千上万种语词被吞噬。 在卡尔梅克,主要居民是四卫拉特蒙古人,他们在三百年前迁居伏尔加河时并不自称“卡尔梅克”,就像半个世纪前尧熬尔人并不自称“裕固”。 无论是小小的游牧族群尧熬尔人,还是卡尔梅克蒙古人,他们都是在内亚草原游牧的阿尔泰语系的族群,他们都生活在欧亚大草原的最前沿,一个在东欧伏尔加河畔草原上,一个在内亚的吐蕃高原边缘山中。一个在东一个西。生存环境是天地之别,历史经历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语词的战争中有一点是相似的。 语词的战争和融合,在人类有了灵魂、舌头和耳朵后就开始了。我从生下来就置身在语词的战争和融合中。 ……在马马耶夫山岗那边,在多瑙河,从飞着白色海鸥的伏尔加河到秃鹫展翅的祁连山,在西伯利亚,在四大洋五大洲……语词的战争没从来没有停止。 如今的卡尔梅克草原就是公元前的萨尔马提草原,是匈奴王阿拉提拉的战场,是术赤的后裔金帐汗国马麦汗的战场,是十六世纪卫拉特蒙古人的草原,是二十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历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卡尔梅克人 卡尔梅克的夜深沉无比,我在梦中呼喊着天上的星星,我把我的梦呓略加删节和修饰,就像一首摇滚歌谣: 玛勒奇奥登——牧人之星。/道伦布尔汗——七神。/阿勒腾嘎达斯——金钉。/浩日软玛日勒——三只母鹿。/星星上有乌托邦么?/星星能为地球上的众生伸张正义么?/星星能救人类么?/星星就是仁爱和平么?………… 人的语词神的语词魔鬼的语词都在我的头顶呼啸,不停地穿越这个世界。语词从嘶哑哽咽的喉咙发出,从地球的五脏六腑发出,深入人的内心深处,直达死亡。 在夏日塔拉小屋 我们的这个草原小镇位于巴彦哈喇山脉东边山脚下。我们的“夏日塔拉小屋”在小镇的最西头,这个小屋是我父母馈赠我们的,由ANUU改建装修而成,院子在一座小山冈脚下。我在夏日塔拉小屋院子里扎下了一座黑帐篷和一座白毡房,是对过去游牧生活的纪念。看着眼前的黑帐篷和白毡房,太多的回忆和思索涌入心头。 昨夜我又梦到了我们家的那座黑帐篷。多少年来,我们的家就是一座用牦牛毛织成的黑帐篷,自从我们一家结束了黑帐篷游牧生涯后,黑帐篷在我的梦中成了一个象征或隐喻,黑帐篷仍然将伴随我一生。每一次看着黑帐篷和白毡房,回想宛若昨日的牧人生涯。往日的岁月和消失语词就会接踵而至,令我迎接不暇。尽管我出生在一座白色的毡房中。1963年的春天母亲在白毡房里生下了我,但是那个毡房我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我只是听母亲很多次讲述那座毡房。而在黑帐篷里我渡过了整个童年、少年时代。 从我们的夏日塔拉小屋往西北边走几百米,再拐进小山沟就是几年前修建的白塔和小寺院。从我们的小屋还可以遥望西边的巴彦哈喇山梁,山梁最高处是我们鄂金尼部落的鄂博。巴彦哈喇山梁在本地汉语中叫做“黑山”,巴彦哈喇是蒙古突厥语,意为“富饶而黑色的山脉”,“哈喇”一词除了黑色之外,仍有“伟大、神圣和巨大”等意思。我认为这信山脉被称做“伟大、神圣和巨大”,是因为祂看见过太多的地狱和天堂,是因为祂饱浸大地上的苦难和幸福。 巴彦哈喇山脉是祁连山东端北麓的一个小支脉,横亘在夏日塔拉草原的中部。 四月的黄昏,小屋的外面狂风大作,大雪飞舞。从窗子里看见院子里的云杉和杨树像疯了般地摇晃,鸟儿都躲藏在草丛中。走出门顶着风雪向西瞭望,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令人热血沸腾的暴风雪从巴彦哈喇山梁那边狂奔而来。 我们进屋后听着暴风雪的声音看书,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听到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老黑猫。它喵喵叫着好像在乞讨食物或是躲避暴风雪。我从冰箱里取了一点松软的煎饼出来,黑猫的不远处还有那只栗色猫和黄猫,老黑猫和栗色猫都吃了煎饼。 夏日塔拉小屋的黑猫家族 老黑猫和栗色猫都是流浪猫,这几年我们常喂这几只流浪猫,它们也习惯了我们。有几只猫会敲门,老黑猫是其中之一。我曾几次听到好像有人敲门,我开了门后看见门外只有老黑猫,当时我不相信是老黑猫在敲门。有时在夜间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们迷迷糊糊地听听动静也就睡着了。 暴风雪还在狂啸,看着窗外的大雪和狂风,我用木柴和牛粪烧了壁炉,煮了羊肉。我和ANUU围着壁炉,看着窗外边吃肉边喝肉汤。壁炉里的柴和牛粪在熊熊燃烧。不知有多久了,没有遇到过这么肆烈的暴风雪。比起和煦的蓝天丽日,这样的暴风雪似乎更接近我生命的本质。 一会儿,我开门看了一下,那几只猫也许躲藏到了院子里的黑帐篷里。平常在空荡荡的黑帐篷,除了几个早已不用的牦牛鞍子和一个銹迹斑斑的铁皮羊粪炉子外什么也没有。那里成了几只流浪猫的栖身之处。 我醒来后从小屋的窗子里看见天晴了,世界一片银白。院子里的黑帐篷、树和小屋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太阳升起来时,积雪开始融化,毕竟是春雪呵。再遥望西边巴彦哈喇山梁,那里悬崖上的积雪也在融化,露出青黑色的山岩。而西南边祁连山的神峰阿米岗克尔依旧覆盖着厚厚的白雪。 “河谷中的笨蛋们,让我去马马耶夫山冈吧!”这个声音又在我的耳旁回响。为了大自然的荣誉,为了受难的语词,为了乌托邦…… 闭目打坐时,我的眼前浮现出年秋天。秋季的彼得堡和涅瓦河。雨在不停在下,我们去了彼得堡的藏蒙佛教寺院,这个寺院是布利亚特蒙古人修建的,寺院建筑是俄罗斯-吐蕃特-印度-蒙古混合型的,院子里的墙面上有阿旺·道尔吉耶夫等蒙古高僧的雕像,寺院内俄罗斯佛教信徒占多数。布利亚特蒙古僧人带我们去餐馆,我们在寺院餐厅吃了布利亚特肉包子。和一个面貌清秀的泰国僧人聊了会儿,他来这个寺院已经有十多年。 汹涌沉稳和恢弘的涅瓦河,层层白浪拍打着一尘不染的水泥堤岸,从波罗的海吹来的风在彼得大帝用斧头砍木做船的青铜塑像上,在彼得堡大学,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萨哈罗夫的塑像上呼啸。 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分院东方研究所,很早以前是沙皇家族的舞厅,外部陈旧的墙壁虽然在脱落,但房屋里面气势雄伟。三位曾在埃利斯塔和我们一起参加过会议的俄罗斯女学者接待我们,他们中只有叶莲娜会说蒙古语,他们带我们参观了馆藏的部分资料。高大的书柜中,除了俄文和其他文字的资料外,还有大量的蒙古文、吐蕃特文、汉文等写本,还有托忒蒙古文的《般若十万颂》和《卫拉特-蒙古法典》,这让ANUU爱不释手,她久久站立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这个百年单传的婴儿般珍贵的文献。 那是用猩红和乌黑的颜色书写的文字,手写体和印刷体的文献装帧和插画令人头晕目眩。如果不是有人这样珍藏,我们还会不会在今生看到这些稀世珍宝呢。 据巴兹尔说,上世纪初在中国西北中蒙交接处割据为王的黑喇嘛丹比加参的头骨也在这个研究所收藏。 腾格里·腾格里 我要说得仍然是内亚的一个小小的游牧族群——尧熬尔,如果以这个小小族群为个案说起,那么他们同样承受了沉重的史诗般的历史和苦难。 古代的斯基泰——匈奴是整个内亚文化的发源处,是内亚族群思想和精神的主脉。 在祁连山这个亚欧草原的前沿地带,在尧熬尔这个边缘族中,他们曾经使用的古代蒙古语和突厥语渐渐演变为俚俗方言。又经过一遍遍的刷洗,那些语词和理念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人的思维。在语词的战争中,语词往往改变人。不同的族群将不同的语词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 比如“裕固”或“回鹘”或“畏兀儿”,还有姓氏、名称和地名的改变。新的名字和原初的空间是脱离的。人们,首先要学会的是胜利者的语词,而把祖辈的语词先放在梦里。他们和北方诸族的血统及心灵,就是斯基泰-匈奴这个最密切的联系渐行渐远。 一次次的逃亡,他们那些基于血液的关键词也在一同消失,千百年来的表达在一夜之间消失。时代的困厄,使人们不再使用那些神圣的语词。人们只能接受胜利者和强大者的语词。人们机械地接受着吸呐着他们的语词,不知不觉地接受一个个最初还很陌生的行为、观念和思维习惯,按照他们那样去生活。语词被人们琐屑的日常生活毁灭,芸芸众生总是不加思考地鹦鹉学舌,附庸风雅。有生命力的东西被机械化。 萨沙和儿子腾格斯 萨沙和巴岳持·拿木琪 夏天,卡尔梅克语言学家萨沙来到我们的夏日塔拉小屋,他在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尧熬尔语词。他的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除了面包和茶就是工作和学习。他的儿子腾格斯在小院里和尧熬尔小男孩苏穆尔沉醉在玩耍中。我们请来杨哥部落的尧熬尔民歌手巴岳特·拿木琪演唱民歌。 深远瑰丽的苍天呵,/在那高处冉冉升起了/十五的月亮/ 呵,十五的月亮 …… 巴岳持·拿木琪和她的徒弟,尧熬尔姑娘弘吉拉特·巴图恰安一首接着一首唱起来了。其中还有那首著名的《阿勒泰杭盖》。 阿尔泰杭盖呵,地势是那么的高/劲壮的骏马呵,是腾格里的马驹 …… 又是“腾格里”,这是个内亚族群的专用词,也是信仰萨满的族群专用词。从伏尔加河畔到祁连山,从北冰洋河口中、西伯利亚冻土带到吐蕃高原和伊朗的游牧集团都在把这个词念叨不止。 张承志在《沉默与公开》中说“……而古代的牧人意识到了。他们以“天”来形容唯一和无限,一个关于崇拜的词,Tengri(腾格里),在从突厥到蒙古的语言中出现”。 这一个语词曾将整个内亚的人民的精神提升到了宗教的范畴,这个蔚蓝色的场景和粘着语词发生着神秘的作用。整个内亚沉浸其中,这一名称让太多的事情昭然若揭。在泰加林边,在贝加湖畔,在鄂尔浑河畔,在于都斤山梁上…… 呵!语词 夏日塔拉的深秋,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逃亡者手记》已经杀青,在写名称索引拉丁字母转写时,我找到语言专家巴图格日乐和精通尧熬尔语的卓玛核对。 如今把这些语词,这些寓意已经弱化了的神圣语词找回来,放在从前的语境里,凹显出了特殊的意义。那些和远古的祖先精神上的关联,还有他们的记忆都随之复活了。 仍然需要一个人面对这语词的战争和风暴。我在自己手稿中日夜呼喊,那个古老的族群之箍和生命符号〓〓。我在梦中常常用自己的母语喃喃低语…… 每当这个符号在人们耳旁响起时,人们面前轰然打开的是一个遥远的英雄时代,一个奇异的精神结构和思想。有多少意义是对这个符号的回忆中创造的呢?不管怎样,都要从人性的基本态度出发去了解。这一个词的运用,意味着重新继承了这一个古老族群和他们的历史姓氏,意味着这个族群有人在努力靠近自己的本质或内核。喇嘛们常说“语词就是神,写错或亵渎一个神圣的语词是要受到惩罚或报应的”。 语词的英雄时代在向我召唤。 然而有多少感情和语词也一同变成了化石,也许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早已南辕北辙的东西,也许这一切不会与先辈们发生任何联系,也许古代完美的精神和灵魂教养早已是昨日黄花。我的眼前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因长期缺少盐而病入膏肓的虚弱肌体,是一个个心灵受到重创的人们。边缘小族群就是一个个大时代的化石。 新时代以一个个语词,一句句的话语,还有铺天盖地的常用语和无孔不入的句型,代替了那些原有的语词而潜入人们的肉体和血液。语词比子弹更具杀伤力。语词也有獠牙、尖利的爪子和血盆大口。语词带着或是善良或是凶恶的种种感情。“语词就是微小剂量的,你吞食了它后,过一段时间才会显露出它的毒性……”这是德国的犹太语文专家维克多·克莱普勒的话。 一种怪异的雾障在侵蚀着所有的人。有些语词被丢弃了,有些语词被膨胀,有些词在被滥用。新的语词将对人的蔑视和其他犯罪合法化。随着一些语词的消失,人们会变坏,崭新的罪恶如火如荼。膨胀和滥用的语词像一群黑压压的牛虻像千万匹鬣狗。屠杀、压迫、抢劫和毁灭。这些语词的风暴将我们覆没使我们窒息,席卷一切,似乎要将所有的族群卷入那个黑暗巨大的公共墓穴。 从高山大河,原始森林、冻土带、沙漠戈壁和大海上又冒出无数美的语词,像子弹一样穿越时空,像晚霞像彩虹像群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langtuhao.com/ylthdt/338.html
- 上一篇文章: 又一位电影大师去世了,他让我们重新发现伊
- 下一篇文章: 安全信息动态印尼伊朗南非菲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