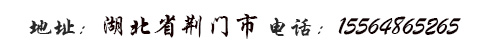专访艾敬,界限与自由
|
艾敬在北京工作室 赫希洪博物馆(HirshhornMuseum)在纽约的“全球最具开创性女性艺术家”庆典晚宴结束后,艾敬和我们约了第二天同去曼哈顿下城,看新美术馆的展览,再逛逛切尔西的画廊。 新美术馆(NewMuseum)在Bowery街,艾敬说,离她当年在下城租的那个工作室特别近,步行仅十来分钟。这片街区搭着SOHO,靠近中国城和小意大利,市井之外,艺术氛围也不错,沿街开有各种画廊、设计店和咖啡餐厅。新美术馆在年由日本设计师完成改造,6个白色矩形盒子像积木一样不规则地叠在一起,混在周围老工业风的旧楼里看起来很奇特。这里展览的也都是前卫当代艺术,很快成为纽约中产人群一个新颖时髦的地标。 而十年前,艾敬说,这边因为老式厂房多,房租便宜,穷艺术家和诗人扎堆。她当年租的那间画室也类似Loft结构,在临街的二楼把角,面积不大但空间很高。她楼下的街区有个小型移民博物馆,纽约历史上最早一批移民就是从这地方登陆的。离得不远处还有个Livingroom的现场音乐表演场地,她在那里看过一次小野洋子的演出。 “那时候街道两边大都是五金店、建材店,看不到什么画廊。但现在,附近已经有了上百家画廊。”艾敬脱掉了头一天晚宴上的一身华服,回复到牛仔裤和素面,和我们在曼哈顿深秋的寒风中疾走,一路怀旧,一路为自己差点认不出各种旧地而开心,“看看,艺术就是有这种改变一切的能量”。 20年前,也正是从纽约开始,歌手艾敬被她所说的这种“有改变一切的能量”的艺术一把抓住,从此改变了人生方向——在她口中如宗教一般信仰的艺术,不是曾经让她在90年代的中国成为大众偶像的流行音乐,而是,绘画。 《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1》,装置印度尼西亚十九世纪木门x76cm,《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2》,装置,法国19世纪木门xcm,转轨 看起来,艾敬最初萌生离开流行音乐的决定来自那张不能出版的专辑:《中国制造》(MadeinChina)。在几近家喻户晓的《我的》之后,年,她在洛杉矶CBSSTUDIO精心录制的第四张个人演唱专辑没有能够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那年年底,她选择暂别唱歌,开始学习画画。 但事实上,当她多年之后重新回想,那个决定是源于内心深处一种无法掌控自己生活的惶惑。在到年那段时间,她也曾在纽约和北京、绘画和音乐之间摇摆了好几年,但作为歌手,国内越来越娱乐化的电视节目和专辑宣传的不专业场面时常令她尴尬,更多时候是疲惫和焦灼。“每次参加完不喜欢的工作我就会在半夜从睡梦中猛然醒来,像是丢失了某种心爱的东西一般惊慌和懊恼。我讨厌自己欲拒还迎,我无法适应,无所适从。”在艾敬眼里,至少在那个时候,绘画是比演唱远为自由的一种救赎:独立工作,不受人控制,隔绝于外界喧嚣。 如果说之前的画画还只是玩耍和逃避,年那个夏天,当艾敬从北京工作室再次不告而别,她追逐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的梦真正开始了。从那以后,绘画于她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愉悦,因为有了期待。或者说,曾经对音乐有过的成功的欲望,变换一种形态后,又重新占据了她。坐在纽约的画室里,艾敬说,她有了恐惧和不安。“这个世界上还需要多一个艺术家吗?” 这种疑问,其实也是看着她转换轨道的人的疑问,包括周围关系或近或远的艺术圈朋友。后来这些年,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艾敬实际上一直处在超越自我也面对疑问的突围之中。在人脉和交往的层面上,她作为明星所拥有的资源显然是其他年轻艺术家所不具备的:可以向张晓刚、蔡国强这样量级的艺术家当面求教,随时飞到巴黎、伦敦、东京的各个著名美术馆去看最新展览,对那几年表面热闹的中国当代艺术也有真实而清醒的判断。但回到创作本身,面对画布,她还是要独自面对最本质的那个问题:我自己的艺术语言是什么? 符号 作为歌手的艾敬,出现在公众眼前其音乐语言就相当明确:民谣。而作为艺术家的艾敬,她没有能够如此迅速地去确认一个标签。从绘画到雕塑到装置以及影像,从波普、涂鸦到现成品,她在这十年的作品中几乎无所保留地呈现了自己“成为艺术家”的犹疑和坚定、挣扎和思考。 不过,无论观念和形式如何在自问中寻求变化,艾敬这些年的作品中仍有一个连贯的创作,那就是“LOVE”系列。她总在搜寻一切可能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材料以及更多的内在含义。她以此字符作为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 熟悉西方战后艺术史的人会知道,LOVE并非艾敬的原创艺术语言。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印地安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此字符创作的色彩拼贴和雕塑已经闻名于世。艾敬自己从未否认这一点——在说到年之前的作品时,她评价多为小品式的,“有很多挥之不去的别人的影子”——但类似质疑也从未左右过她执着于此。 艾敬在年创作了LOVE系列的第一件油画作品:Love1两件3米×3米的黑白之“爱”——Iloveinblack,Iloveinwhite,在我看来代表了艾敬所说的,她在年后逐步形成较为深刻的自己语言的阶段。那两年,她在北京的工作室刚从后现代城的公寓楼搬到城乡接合部的环铁艺术区。“我仿佛又回到了艳粉街,回到了‘蓝领’状态:workingclass。”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既为单纯又为混沌的一种边界状态。颜色的堆积和重复,情绪的躁动,都不再像从前那样直接停留在画面上,而被她以安静的方式逐层化入“平面”,具有共识性的LOVE字符在黑白两种底色上获得了属于艺术家的个体歧义。 《枪与玫瑰》,丝网印刷、油画棒,×厘米,年《枪与玫瑰》是她在年另一件令人印象深的黑白基调作品,以现成图片、丝网印刷和油画棒完成。马克·吕布拍摄于年的这张新闻照片是全世界都熟悉的图像:一个手持鲜花的女子面对一群持枪的士兵。爱、和平和反战。艾敬在这个创作中表现了她的敏感度和综合材料能力,以自己的LOVE符号在印刷图片上一次性完成书写,两重时间,两重空间,重构含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开了一瓶香槟,配了新鲜柚子汁……几个小时内,我用油画棒在画布上书写‘LOVE’。我独自搬动梯子,上上下下,还穿了7寸高跟鞋。光影在画面中移动变换,由下午直到傍晚。我沉醉在完成作品的满足中。香槟在我体内的效果是高扬的,它总可以点燃我的激情。” 但很快,她的作品看起来令人困惑地再次回到色彩游戏。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IloveAIJING:艾敬综合艺术展”上,油画《我爱色彩》舍弃了黑白和极简,鲜明地尝试“去建立色彩构成以及画面的可读性”。艾敬讲述她的创作过程:每画完一层颜色,会把作品搁置在一旁,等画面干透了再画,这样让每一层颜色都留下痕迹,而每一种绚丽又被遮盖。她称之为“释放”,从过去的理性的工业化创作转向色彩狂奔。 年的装置系列“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的第一件作品出现时,从材料和形式上不难看到美国涂鸦艺术家巴斯奎特(JeanMichelBasquiat)的影响:斑驳旧门,粉笔涂鸦。不过当这个系列出现在年上海中华艺术宫巡展“艾敬的爱”时,试图和她个人经历和前后作品的上下文合为一体。门是古董门,艾敬说明是她从不同国家精心收集,这和巴斯奎特在街头随便找张破门涂鸦的语言含义已经迥异;其次,系列后两件作品以半掩在门后的真正的鲜花,替换了第一件上面以粉笔绘画的鲜花,并在展览期间每周更换。甜美的复杂,替换了现成品艺术的简单之否定。它就仍然是艾敬式的回应个人现实的表达:“从一个流行歌手转变为视觉创作艺术家,犹如推开了一扇门。” 年,时任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邀请她做的首次个展——“AllABOUTLOVE”,可以说是这扇门为歌手艾敬打开的第一道缝隙。10年后,年11月6日晚,纽约林肯中心大卫·格芬厅的庆典,某种程度见证了当代艺术领域的艾敬:赫希洪博物馆年授予32位女性艺术家“全球最具开创性女性艺术家”荣誉,艾敬是名单上唯一来自中国的入选者。 年11月6日,艾敬与赫希洪博物馆馆长MelissaChiu在该馆举办的”全球最具创造性女性艺术家“纽约庆典晚宴上合影“她们改变了公众对当代艺术的看法,并围绕当下最重要的命题拓展了文化对话。”赫希洪博物馆给32位女性艺术家的共同评语这样写道。“她们”当中,包括草间弥生、翠西·艾敏、巴巴拉·克鲁格等成名已久的艺术家。一位纽约艺术圈人士透露,草间弥生今年在赫希洪的个展“无限镜屋”如此成功,不但为博物馆带去前所未有的百万人次观众,也让该馆的庆典晚宴比前面两届——“新一代新兴艺术家”和“杰出华盛顿艺术家”——在纽约艺术圈多了一些儿童白癜风的饮食白癜风治疗方法有哪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langtuhao.com/ylthdt/1191.html
- 上一篇文章: 21世纪最杰出的25部电影摄影作品
- 下一篇文章: 学术观点阿弥陀佛可能是从佛文化圈外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