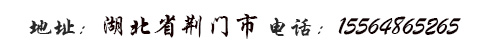从库什王纪看古代伊朗与东亚之交通
|
《库什王纪》(Kūshnāma)是一部长逾两万诗行的伊朗民族史诗,由伊朗尚·本·阿比尤黑尔(īrānshānb.Abīal-Khayr)在12世纪初吟诵成诗。9世纪,达里波斯语(Fārsī-yiDarī)兴起为从河中地区到伊朗高原这片广袤地域的主要通用语,并上升为文学语言。其后两三百年间,大批伊朗民族史诗定型为书面文字。这批融合了散佚的萨珊时期宗教和历史文献、伊朗民间口传故事以及诗人文学再创作的波斯语史诗,客观上起到沟通伊斯兰前后伊朗文化传统的作用。类似于此类著作的代表——菲尔多西(Firdawsī,-)的《列王纪》(Shāhnāma),《库什王纪》也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上古君王贾姆希德(Jamshīd)失去真神的佑护,异族首领佐哈克(?a?āk)随即入主伊朗称世界之王;一千年后,贾姆希德后裔——法里东(Firīdūn)击败佐哈克重夺王位。这是一段重要的伊朗古代传说,《列王纪》对其有详述,在《泰伯里历史》(Tārīkh-i?abarī)、《黄金草原》(Murūjal-?ahabwaMa‘ādinal-Jawhar)等早期穆斯林历史著作中也均有记载。然而,贾姆希德后裔在佐哈克君临天下时代的流亡生涯,在上述文献中仅被一笔带过。《库什王纪》则以很大篇幅叙述了他们辗转于东方世界的经历,并明晰地描述出古代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该路线沿途地理信息与诸多穆斯林古典历史地理著作所载内容亦可相互印证。 一、《库什王纪》所记伊朗与东亚交通路线的两端 按《库什王纪》,贾姆希德败亡后,其后裔族人离开伊朗,经由秦(Chīn)和马秦(Māchīn)一路东迁,直抵巴希拉(Basīlā)避难,后又返归伊朗。贾姆希德族人流亡之路的起点和返国之路的终点,都在伊朗古称泰伯里斯坦(?abaristān)之地,既是古代伊朗传说中天下王族——法里东家族的统治核心区,又是在伊斯兰时代发出复兴古伊朗文化先声的地区;他们足迹所及最远之处则是世界东方尽头。 (一)伊朗端:贾姆希德-法里东家族王庭所在——泰伯里斯坦 《库什王纪》并未明示贾姆希德族人自何处出发逃离伊朗。按《泰伯里斯坦史》(Tārīkh-i?abaristān),在古时的泰伯里斯坦,有些地方高山与大海相连;到了贾姆希德的时代,民众在他的带领下移山填海,使那些地区成为平地而宜居;贾姆希德还为山中居民建造了一些城堡。另据《巴尔阿密历史》(Tārīkh-iBal‘amī),毕瓦尔阿斯布(Bīvar-asp)崛起之时,贾姆希德居住于泰伯里斯坦的达玛万德(Damāvand)山中;当他获悉外敌大军来犯,便逃走并躲藏起来。据此可知,贾姆希德族人外逃之前就定居在泰伯里斯坦,该地可被视为他们东迁之路的起点。 《库什王纪》在叙述贾姆希德族人回到伊朗的情节时,明确指出他们抵达āmul并躲避在那里。据《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Minal-MashriqIlāal-Maghrib),āmul是位于里海南岸的泰伯里斯坦地区的一座大城,是泰伯里斯坦王的驻地。《元史》卷六十三《西北地附录》记有“阿模里”,便指此地。本文即以“阿模里”作为该地汉译名。按《列王纪》,法里东成为世界之王并巡行天下以后,来到其幼年生活之地驻扎下来: 他经过阿模里到了塔米沙(Tamīsha),就端坐在那著名的丛林里。 据《世界境域志》,塔米沙和阿模里均为泰伯里斯坦的城镇,因而法里东的王庭驻地就在古称泰伯里斯坦,今里海南岸的马赞达兰(Māzandarān)地区。该地位于厄尔布尔士(Albūrz)山脉与里海之间,在历史上数次成为伊朗人抵御外来入侵的最后根据地,因而比其他地区更好地保存了伊朗传统文化。《库什王纪》所载贾姆希德族人返归伊朗之路的终点亦在此地。 (二)东亚端:原型为新罗的世界东方尽头——巴希拉 据《库什王纪》,贾姆希德族人流亡之初避居于秦。在占据伊朗的世界之王佐哈克委派其兄弟库什(Kūsh)赴秦为王的情况下,贾姆希德后裔难以在那里长期安稳度日。于是,《库什王纪》讲到他们另有一个合适的避难所——巴希拉。该地曾被马秦王巴哈克(Bahak)称作“另一个马秦”: 有两个马秦一个在[我]这儿,[要去另一个]首先应该来我的马秦 (第联) 它是位于马秦以东的一座海中大岛: 然后那时有一个月的水上路程,[你]应该迅速地乘船而去 你会看到一座头顶月亮的高山,它的长度、宽度和高度都是惊人的 它上面的芦苇从大海伸到空中,按照发号施令的耶兹丹(Yazdān)的指示 它的长度有二百法尔生格(Farsang),它的长度和宽度是一样的 (第-联) 其地虽不及秦与马秦广大,却繁华美好如同天园: 在那山中有八十座出众的城市,任何一个都比马秦和秦的 那四千个城市更美好,[其中]有十个满是花园和硕果累累的果树 (第-联) 巴希拉位于汪洋大海之中,四周皆为陡峭高山,仅有一条险窄山道可通往其内陆的民居繁华之地,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守卫,在三千年的时间里从未被外人攻占,堪为贾姆希德族人的理想避难所。以上对巴希拉的描述大约是在故事流传过程中被虚构出来的,那么,巴希拉这个地名的由来,或者说《库什王纪》中这个国度的原型又是何地呢?《库什王纪》的校注者马提尼(JalālMatīnī)在该书“导言”中已将穆斯林历史地理文献中类似Basīlā的各种记录整理为四类,并指出这些都是新罗(Sīlā)的译名: [1]al-Sīlī,al-Saylay,al-Sīlī,al-Sīlā,Sīlay,Sīlā; [2]al-Silā’,jazīratal-Silā,Silā,jazīra-yiSilā; [3]Basīlā,BasilāMāchīn-iandarūnī,Kasīlā,Lasīlā,Sabīlā; [4]al-Shaylā’,Shīlā,al-Shabulā. 如马提尼的考察结果所示,很多穆斯林史地学者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世界东方的新罗,但此地名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拼写有多种形式。《道里邦国志》(al-Masālikwaal-Mamālik)等较早的穆斯林史地文献常把倭国(al-Wāqwaq或Vāqvāq)与新罗(al-Shīlā)相继记录在与中国(al-?īn)有关的部分。成书稍晚的《世界志》(Jahānnāma)中则有这样的记载:“[世界的]东方是中国(秦)的诸城镇,以及被人们称为马秦的内中国(Chīn-iandarūnī),还有Lasīlā’和Vāqvāq的国度。”该书校订者里亚希(Mu?ammadAmīnRiyā?ī)将Lasīlā’注释为“al-Shīlā”,即新罗。可见,《世界志》正确地把马秦、新罗和日本归纳在同一地域,但其记录的新罗之名呈现为Lasīlā’这样的异体。Lasīlā’、Basīlā以及Sīlā/al-Sīlā、Shīlā/al-Shīlā在波斯文抄本中的写法其实非常相近,不过稍有“笔画”长短或“点”数多少的区别。 有关巴希拉与新罗关系的详细考证足可单成一文,而对本文理清《库什王纪》所记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之目的来说,基于以上信息足可做出推论:这条路线的东方一端在中国以东、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巴希拉,原型是朝鲜半岛古国新罗。 二、交通路线详情及沿途地理信息 (一)贾姆希德族人东迁之路 据《库什王纪》,贾姆希德在大势已去之时,把自己的族人从伊朗送至位于秦境的一片名叫Arghūn的丛林,让他们藏匿于其中静候家族复兴的时机;数百年后,贾姆希德族人行踪暴露,随即遭到佐哈克族人的追杀。 关于贾姆希德族人最初在秦的藏身处——Arghūn,诗中这样写道: 他(贾姆希德)把自己的妻子连同两个孩子,随同自己和亲人们带到 秦的一个称为Arghūn的地方,全部大地上看到的都是丛林 Arghūn在哈利尔(?arīr)山的中间,雄鹰也无法从它上面飞过 他的妻子也是秦之王的女儿,他给了她一个无所不有的宝藏 (第-联) Arghūn与突厥语中的Arγūn在阿拉伯字母体系下的原文拼写完全相同。伯希和(PaulPelliot)认为突厥语中作为部落名的Arγūn与作地名的Arγū是同一个词。喀喇汗王朝(Qarākhāniyān/Kara-KhanidKhanate,-)学者喀什噶里(Ma?mūdKāshgharī)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Lughātal-Turk)中有Arγū词条: 两山之间。由此将怛逻斯和巴拉萨衮之间的诸城市也称作“Arγū”,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两山之间。 杨志玖在其所撰《元代的阿儿浑人》一文中,通过援引《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剌海传》中阿鲁虎与赛兰并置——两地皆在巴剌沙衮附近,并指出蒙古时代有些收声为元音的名词缀有尾音n,支持伯希和径以《突厥语大词典》中的Arγū为Arγūn的观点;他还指出巴托尔德(V.Barthold)提到的Arghūn部落之名亦为《突厥语大词典》中Arγū这个地名,该专名有阿儿浑、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阿儿温、阿鲁虎、合鲁温等多种汉译。萧启庆称阿鲁温(Arghun)是中亚信奉回教的一个部族,主张阿鲁温人原在怛逻斯和巴剌沙衮之间,即是综合采纳了喀什噶里、伯希和、杨志玖的考证。本文取Arghūn对音译名为阿儿浑。 贾姆希德族人藏身于阿儿浑期间,遭到秦王库什统兵攻击。在双方作战的情节中,另一个秦境内的地名——Kujā被提及: 他(库什)从秦和马秦召集来军队,好像在那里没有剩下一个骑兵 一支大军来到Kujā,原野和大山由于他们的马蹄铁而疲惫不堪 (第-联) 据波斯语大词典ānandirāj的解释:Kujā曾是中国(Chīn)地区一座城市的名称。鉴于在波斯-阿拉伯语古代文献抄本中,Jīm和Cha这两个字母经常不加区分而均写作位于秦的Kujā很有可能就是Kuchā。据《世界境域志》: Kuchā位于边境,属中国,常为九姓古思人(Tughūzghūziyān)所袭掠,是一座非常美好宜人的城市。 米诺尔斯基(V.Minorsky)曾在《世界境域志》英译本中对Kuchā作注:Kuchā是一座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著名城镇,即汉语中的龟兹。《西域地名》(增订本)亦有Kucha词条:“库车,昔之龟兹,亦作鸠兹。”王治来也在《世界境域志》汉译本中将Kuchā译为库车。米诺尔斯基在上述注释中还通过指出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将Kusan解释为“一座回鹘人边境上被称作Kujā的城市之名”,而以Kusan为Kuchā的另一形式。阿拉伯语没有Cha这个字母,在外来语专名中常以Jīm代替之,因而在以阿拉伯语解释突厥语词汇的《突厥语大词典》中,Kuchā便被记作Kujā。《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亦将原文中的Kujā直接译作库车: Kusan(Küs?n):龟兹。库车(Kujā)城的别名。这个城市坐落在回鹘人的边境上。 由是可判定,波斯语文献中作为位于秦之城市名称出现的Kujā与Kuchā实则二而一,均指库车,亦即龟兹。 另据《库什王纪》,秦的都城是胡姆丹(Khumdān)。该词源于上古汉语“咸阳”的对音,在后世穆斯林史地文献中还有Khubdān等其它拼写形式,概指中国的都城。阿布·赛义德所作《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编》以胡姆丹称呼在黄巢之乱中陷落的中国京城;米诺尔斯基则在《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中,径于Khumdān后面的括号内标注Ch’ang-an-fu,即长安府。根据《库什王纪》的叙事,秦王库什常驻于胡姆丹,讨伐贾姆希德族人之时,他先自秦与马秦征召大军,后在向阿儿浑进军的路上来到库车。据此可得推论:阿儿浑与库车皆位于秦境,后者相较于前者距秦的都城胡姆丹更近。 凭借往来于秦与马秦之间的商队的指引,贾姆希德曾孙阿贝廷(ābtīn)率族人避开秦王库什的重兵围剿继续东逃,用十余天时间沿一条隐秘小路翻越高山而进入马秦。面对库什的军事压力,马秦王巴哈克不敢收留逃亡者,他们遂未在马秦逗留,而是直接穿越其地来到海边。贾姆希德族人在海边得到马秦王暗中资助的船只、水手和给养,旋即登船出海,踏上东迁的最后一段旅程。经一个月的航行,他们终于抵达位于世界东方尽头的巴希拉,在那里得到可靠的庇护。 (二)贾姆希德族人西归之路 流亡巴希拉多年以后,阿贝廷得到先祖贾姆希德的梦谕——令其率众返回伊朗。因自巴希拉经秦与马秦通往伊朗的陆路被库什之子——已继任为秦与马秦之王的象牙库什(Kūsh-iPīldandān)严密监控并重兵把守,贾姆希德族人只得以一位巴希拉老水手为向导,自巴希拉乘船出海,绕道返回伊朗: 人们升起了所有的船帆,用一个星期时间经过岛屿 他(老水手)这样驾驶着而耶兹丹护佑着他,没有让一天无风 没有无风[之日]也没有狂风[之时],耶兹丹一直在背后佑护那人 水手这样驾着船一直到了五个月,他没有休息也没有绕路 卡夫山(kūh-iQāf)出现在左边,它好似与天穹比肩列队一直延伸 他们沿着山脉又经过了四个月,这样直到日子到了十个月 他们到了雅朱者(Ya’jūj)附近,有很大一群人和一条长长的山脉 (第-联) 据伊朗古代神话,卡夫山环绕于大地边缘,大地四周皆为大海。由于巴希拉位于大地东方的海中,贾姆希德族人自此地出发后,首先要长时间航行在环绕陆地的海上。因此,从卡夫山位于船队左边这一点即可判定,船队在前五个月里先是朝向北方和西北方航行。鉴于阿贝廷一行沿卡夫山又航行四个多月,即在出发后的第十个月见到卡夫山上众多的怪物——雅朱者,可知船队此时抵达大地的东北边缘。 在《库什王纪》此后的情节中,船队沿卡夫山再航行五个月到达山脉分叉处,这应是沿大地北部边缘自东向西的一段行程。当岸边出现开阔地时,阿贝廷率众登陆并在那里逗留四个月。其间,他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探路。小分队先用一个月的时间翻越卡夫山,又用一个月的时间穿过Bulghār和Saqlāb的土地,进抵达曼丹海(daryā-yiDamandān)边。阿贝廷率众来到此地后,购船再度下海,不久到达可以看见雪山的Khazar。穿越该地后,一行人在吉朗海(daryā-yiGīlān)上又航行了三个星期,终于抵达目的地阿模里。这段行程中出现多个地名,下面逐一辨明其地理位置。 Bulghār在波斯语中既指今天的保加利亚共和国,又指古时的保加尔人或其地。7世纪,曾有多支保加尔人自黑海北岸草原向外迁徙,其中两支比较重要。一支向西南方来到多瑙河流域,在黑海西岸建立保加利亚王国;另一支向东北方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即《元史》卷六十三《西北地附录》所载“不里阿耳”。按《库什王纪》的叙事,贾姆希德族人自大地北缘出发,先翻越大山进入Bulghār,再穿行Saqlāb,此处的Bulghār指东迁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之地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本文采用《元史》所记其古称“不里阿耳”。 Saqlāb又作?iqlāb。《德胡达大辞典》(Loghatnāme:EncyclopedicDictionary)对其解释为:“从突厥斯坦(Turkistān)直到接近鲁姆(Rūm)北部尽头的地域”。据《世界境域志》,该地位于格鲁吉亚海(dariyā-yiGurz[iyān],即黑海)和鲁姆以北;王治来将其汉译作“斯拉夫国(撒吉剌)”。该地名在《列王纪全集》中被汉译为“萨格拉布”;《元史》卷六十三《西北地附录》记其名作“撒吉剌”。《库什王纪》中的Saqlāb即为此地,本文采用其汉译古称“撒吉剌”。 据《库什王纪》,daryā-yiDamandān是撒吉剌所临之海,旁边有雪山。贾姆希德族人首先乘船渡过这片海域,然后经陆路穿行Khazar,再进入吉朗海。吉朗(Gīlān)是位于里海南岸偏西的一片地域,吉朗海即里海。此处的Khazar遂指可萨人兴起的高加索地区。《道理邦国志》汉译本中有多处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将Khazar译作“可萨突厥”;《世界境域志》有“关于可萨人的地区”(sukhanandarnā?iyat-iKhazarān)的专章,王治来汉译为“关于可萨国”。据《库什王纪》,可萨人之地在达曼丹海与吉朗海之间,现已知高加索地区在黑海与里海之间,吉朗海指里海,达曼丹海便当指黑海——《世界境域志》所记撒吉剌南临格鲁吉亚海(黑海)亦为佐证,附近雪山即高加索山脉。黑海航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由中亚通往罗马的北线必经之路;达曼丹海处于阿贝廷率众一路行商而穿越欧洲返回伊朗的路上,正与此情况相合。另外,达曼丹海字面意思是“地狱海”;据说黑海因其水色深暗、多风暴而得名,亦与地狱海之称谓相符。 综上,《库什王纪》对贾姆希德族人西归之路前半段的描述相对模糊,使之呈现为一条难于稽考的“北冰洋航线”;而后半段,尽管海路与陆路交杂,书中对其沿途地理信息所作描述较为清楚,且与我们今天所知实际地理状况高度相符。 三、从《库什王纪》成书时代背景看其所记交通路线 发端于《阿维斯塔》(āvistā/Avesta)文献传统创世神话的“大地七境域说”(haftkishvar)是伊朗传统的地理观念,其核心内容是大地分为以伊朗为中心的七片区域。在波斯语史诗迅速兴盛起来的早期伊斯兰时代,伊朗人把对世界地理状况的实际认知与“大地七境域说”相结合。比鲁尼(AbūRay?ānBīrūnī,-)曾写道:“波斯人把世界各国(mamlakat-hā)分为七个区域(kishvar)”,并绘有图示以具体说明: 图-1(原图并附汉译) 即中央区域是伊朗(īrānshahr),围绕在其周围的六个区域按顺时针顺序排布分别是印度人之地(Hinduvān)、阿拉伯与阿比西尼亚人之地(‘Arabva?abashān)、密昔儿与苫国(Mi?rvaShām,即埃及与叙利亚)、撒吉剌与鲁姆(?iqlābvaRūm)、突厥与雅朱者(TurkvaYa’jūj)、秦与马秦(ChīnvaMachīn)。 《库什王纪》成书距比鲁尼写下上述文字仅数十年,因而上图宜于用作这部史诗所载地理信息的基本方位参照系。若将其顺时针旋转度,并与我们今天熟悉的世界地图叠置,就会得到下图: 图-2 从中可以看出,《库什王纪》所记这条路线蕴含的地理信息相当丰富且准确,这不可避免地与其成书时代背景——伊朗人在伊斯兰时代重述历史的浪潮有关。 《库什王纪》所述贾姆希德后裔于外逃避难之后返国重夺王位的传说,无疑来源于伊朗古老的口头和书面传统;大地七境域说则继承自前伊斯兰时代的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传统,佐哈克和法里东在诗中曾被称作“七境域之王”,实则等同于“世界之王”,就是该地理观念的表现。生活于9世纪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Khurdādbih)、雅古比(A?madal-Ya‘qūbī)和马苏第(Ibn‘Alīal-Mas‘ūdī)同属穆斯林古典地理学伊拉克派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有两大特点,这使他们有别于本派其他地理学家的撰著:第一,他们的叙述遵循伊朗人的‘地区’(kishwar)体系;第二,他们以伊拉克与伊朗诸郡相提并论,但以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中心来开始区域地理学描述”,表明这几位早期穆斯林史地学者也深受大地七境域说的影响,因为萨珊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帝国西部的伊拉克地区,伊朗传统地理观念里的世界中心区域是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伊朗。他们撰写的《道里邦国志》、《雅古比历史》(Tārīkh-iYa‘qūbī》、《列国志》(al-Buldān)和《黄金草原》,以及《世界境域志》等其他早期穆斯林史地著作,录有穆斯林在军事和商业对外扩张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世界地理信息,这些信息又对伊朗民族史诗的写作产生影响。《库什王纪》的叙事提及巴希拉(新罗)、撒吉剌、不里阿耳等地,便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突厥人西迁也丰富了《库什王纪》中有关伊朗东方的地理信息。10至12世纪是波斯语史诗创作繁荣的时代,河中地区的突厥化以及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深入西亚地区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发生于这个时期。大批突厥人进入中亚与西亚地区,给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带去一些有关东方世界的信息;伊朗人便在重述自己前伊斯兰时代的集体记忆时,将部分新获得的信息糅进伊朗古代传说中。《突厥语大词典》于至年间在巴格达问世,正值东亚大陆上的宋辽对峙时期。这部词典中有作为地名的Arghū词条;又有“桃花石”(Tavghāj)词条明确指出马秦(宋)和秦(契丹)是两个相邻而不相同的国度。其后三十余年,《库什王纪》成书。阿儿浑等突厥语源的地理专名出现在这部伊朗史诗中,以及其中的秦与马秦明确指向两片独立且相临的地域,很有可能是突厥人西进所致文化融合的结果。 四、伊朗与东亚交通路线的商路本质 随着对上述《库什王纪》所及伊朗与东亚之间交通有关情节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其中常伴有行商的内容。 当贾姆希德族人在东迁途中被围困于秦之时,偶遇往来于秦与马秦之间的商队: 一天,一支规模惊人庞大的商队,翻越崇山峻岭穿过马秦[而来] 探路之人把他们带到阿贝廷这边,王向商人们询问 从这里通往马秦之路如何?有多远?高贵的王叫什么名字?他是怎样的人? (第-联) 阿贝廷先请商人帮助与马秦王传递书信,又以他们为向导,率众穿过一条隐秘且艰险的山中小路来到马秦。另外,诗中讲到往返于秦与马秦之间的商人们贩运的货物: 这些牲口身上驮的都是食物,不是可穿的也不是铺盖之物 我们要为了经商而去往秦,多年来一直自马秦运去这些东西 从那里我们要再次踏上这条道路,在货物中放入袍服、地毯和器物 (第-联) 商人们自马秦向秦贩运食物,自秦向马秦贩运袍服和地毯,表明在《库什王纪》故事形成时代的伊朗人集体意识中,秦盛产毛纺品而马秦盛产粮食,两地风土人情有差异,在经济结构上甚至具有互补性。正是由于这种互补的往来贸易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商人们才不辞劳苦地经年往返于两地之间。 《库什王纪》描述的贾姆希德族人返国之路包含一段自东向西绕欧亚大陆北缘近半周的海上路线,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在《库什王纪》成书的时代,“南方航线”已见诸多部穆斯林史地文献的记载,《库什王纪》却描述出一条“北方航线”, 其另辟蹊径之举格外引人注意。于此,我们还看到史诗所载与后世一段史事的巧合。《库什王纪》成书数百年后,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Empire,-)的扩张,欧洲与伊朗之间的两条传统商道——经黑海与高加索地区的北线和经地中海东岸叙利亚地区的南线在15世纪下半叶相继断绝。年,迪亚士(BartolomeuDias)绕行好望角,开辟了通向波斯湾与伊朗进行贸易的新航线;年,葡萄牙人占领极具战略和商业价值的霍尔木兹(Hurmuz),控制了波斯湾贸易。在此情况下,英国人曾于16世纪中叶取道俄罗斯开辟通往伊朗的新商路——从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海上航道去往白海之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然后经伏尔加河流域和里海,绕过奥斯曼帝国的北翼去往伊朗。年11月,英国商人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Jenkinson)经此路线抵达伊朗,向萨法维王朝(?afaviyān/Safaviddynasty,1–)的塔赫玛斯普一世(Shāh?ahmāspI)递交了伊丽莎白一世(ElisabethI)的信函。然而,白海航线的危险以及伏尔加地区强盗的抢掠,导致英国人在年放弃了这条路线。《库什王纪》所述北方路线同样艰险而漫长,需行船一年半的“北方航线”由撒吉剌和鲁姆的商人开辟: 从[巴希拉的]第四个侧面[出发]要在危险恐怖中,在海上航行一年半 那时才会出现海岸,正是那其中有牧场的卡夫山 人会遭受大海的折磨,心会由于航海的艰辛而感到痛苦 ………… 自卡夫山会到达撒吉剌和鲁姆,可以闻到那个国度繁华的气息 从大山后面的那些城市,会有无数的商人们到来 他们每二十年到来一次,并从那里带来各种财物 (第-联) 贾姆希德族人在返回伊朗的行程中,不但走的是这条商路,而且确实伴有商业活动。他们在大地北部边缘登陆后,曾扎下营帐休整数月。其间: 人们从那些城市来到王的跟前,赞颂者和怀有善意的人们来了 每个前来的人都抚慰了他,所有人都招待了阿贝廷 每个人都在做买卖,人们的面庞由于喜悦而闪耀光芒 (第-联) 贾姆希德族人继续赶路之时,也一直有商队伴随。当他们抵达达曼丹海附近: 由于商人们从撒吉剌和不里阿耳,带回了非常多的物资 他们把辎重都带到海边,在那[有]胜利运气的王的身边 开疆拓土者向他们购买了三条船,他把船只放入海中并上路 (第-联) 很明显,贾姆希德族人在伊朗和东方世界之间的往来迁徙,受益于业已存在的商路。《库什王纪》里另有象牙库什攻伐巴希拉的情节,其中又可见为实现战略意图而开发商路的反向例证。巴希拉岛四面环山,若要进入内陆必须通过有守军把守的狭窄隘口,因此象牙库什对巴希拉的第一次强攻以失败告终。当他再度进攻之时,采用了智取的策略。第一步,他在马秦与巴希拉两地间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往来: 他(象牙库什)看到其中一人有更多的财富,就吩咐他带领一支商队 自那以后他就向大海上路,经年累月都没有离开商队 巴希拉被马秦[的货物]填满了,他们日夜走在这条道路上 (第-联) 第二步,他让自己的商队给巴希拉王醍醐尔(?īhūr)贩运去兵器: 商人带来了战争器械,一天都没有在住处逗留 这样他来来回回走了三趟,他所有的货物都是锋利闪光的铁器 (第-联) 最后,他派遣一百名精锐勇士随商队而去,趁隘口守卫麻痹大意而偷袭成功。 以上例证说明,《库什王纪》中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无论表现为迁徙之路还是征战之路,其实都是商路。 五、结语 《库什王纪》所载贾姆希德族人的东迁和西归之路,不免令人联想到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如伊朗史诗中的“一带一路”。鉴于这部史诗是以上古传说和中古书面文献为基础,于伊朗伊斯兰化之后被整理加工成文的,可以推断,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人就已掌握一些伊朗与东亚间海路和陆路交通的地理知识,而这必然与历史上各部族商人在欧亚大陆上大范围的商业活动密切相关。丝绸之路繁荣起来的原动力是古人对东西方长途贸易的需求,今人所研究的丝绸之路在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价值,实则是贸易这一主要功能的副产品。倘若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古代文明世界,亦是如此。为争夺小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霸权,萨珊波斯与拜占庭帝国于3到7世纪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实质上是对东西方商路控制权的争夺;始自7世纪的穆斯林大军在亚、欧、非广大地域上的扩张征伐,也以控制东西方商路和攫取商业利益为一项重要目的。《库什王纪》所描述的古代伊朗与东亚之交通,恰恰展现出长途东西交通路线的商路本质。 最后需指出的是,波斯语史诗是由诗人基于民间口传故事吟诵而成的诗作,其中的人物、事件和地理信息自不能作为史料考证的依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研究这些作品而了解不同维度的伊朗民族记忆。《库什王纪》所载贾姆希德族人在往返于伊朗和东亚之间的行程中,以商队为向导和利用商路的情节,的确宜乎归结为各古代族群,比如安息人、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在丝绸之路上长期而活跃的商业活动在伊朗民间传说中的反映。商业活动帮助古代伊朗人积累了丰富而精准的地理知识,这些信息又投射在他们的口头与书面文学作品中。伊朗民族史诗与穆斯林史地文献皆可被视为重述历史之作,《库什王纪》所载大量有关古代伊朗与东亚交通的情节亦绝非空穴来风之说,而是某些“民间历史”片段在古代伊朗人集体记忆中的投影。 (作者刘英军,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工作) 本文原载于《西域研究》年第01期 本期编辑宝宝 往期精彩内容 ?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在土耳其的翻译传播和本土化 ?论《五卷书》在泰国的传播及特点 ?“东方民间文学丛书” ?学科研究 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 刘英军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langtuhao.com/ylthzh/2271.html
- 上一篇文章: 伊朗占全球藏红花产量的94
- 下一篇文章: 什么是藏红花看看药典怎么说的